故乡是一场无法完成的赎还
袁凌

袁凌。
袁凌,生于陕西平利县,单向街2019年度青年作家,新京报·腾讯2017年度特别致敬青年作家,2015腾讯书院文学奖年度非虚构作家。出版《我的九十九次死亡》《青苔不会消失》《世界》《寂静的孩子》《生死课》等书,发表长篇小说《记忆之城》等,作品入选三届《收获》文学排行榜、两届豆瓣年度作品、新浪十大好书、华文十大好书、南方都市报十大好书等。

家乡土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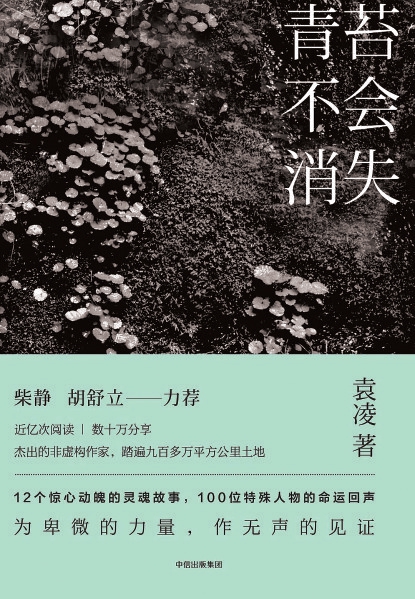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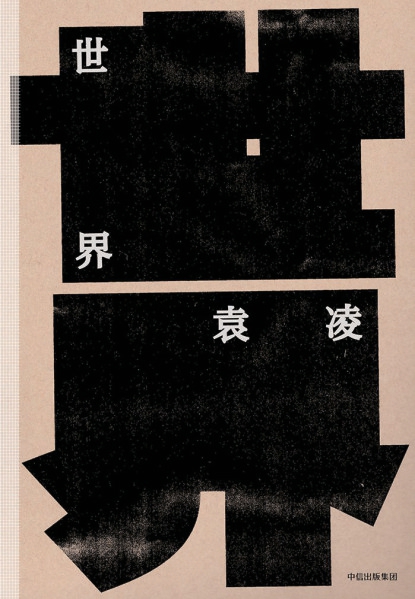


袁凌部分作品封面。
面对故乡,
我唯一的办法是用微不足道的文字来偿还,
即使注定无法还清,
我也无从落叶归根。
一
上个月我回了一趟老家,参加三舅娘的葬礼。
虽然是疫情期间,很多人出门打工也没回来,人依旧不少,也算热热闹闹。三舅娘活了将近八十岁,比我的母亲去世晚了三十几年,也算喜丧了,我的心情却始终有些沉重。
其实从这年开头,我就知道三舅娘的日子不长了。或者说还要早,在她最终离开筲箕凹的时候。一旦离开那个山村,到了广佛镇上,她似乎完全变了一个人,失去了所有的活气。春节回乡,我在汉表哥的楼房里见到她的时候,她恹恹地歪在电炉子旁的沙发上,勉勉强强地认出了我,也懒于询问我的近况,对于大家的聊天完全置身事外。当时我感到,我认识的三舅娘已经死去了,只是还需要一段时间,来摆脱这个躯壳。我知道,她不会拖过这一年。果然她在九月份摔伤了腿,在床上拖拖拉拉了两个来月,就迎来了最终的结局。
大家似乎也在等待着这一天,终于松了一口气的样子。丧礼上没有一个人掉眼泪,烧纸也不殷勤,转灵的人到半夜不剩两个。第二天送棺材上筲箕凹安葬,五个子女各忙各的,到了筲箕凹没人放鞭炮,落土时发现连火纸线香都忘了带,不得不临时联系人再从广佛镇买了捎上去。我感到这场葬礼有些不得体,和小时候那些虽然寒俭却隆重的丧事不一样。
随着三舅娘的逝去,我感到和故乡的血脉联系又断了一根,而且是很重要的一根。我们两家挨着,堂屋共用一面土墙。小时候,三舅娘拿自家的窝窝头给我们吃,那时我家一年到头吃不上干饭,只有玉米糊糊掺洋芋。三舅娘和母亲的关系最亲近,有最多的话讲。当所有人在城镇化搬迁中渐次离开山村,包括年纪更大的大舅、大舅娘和二舅娘,山村空了下来,她成了最后一个留守的人。
“街上哪里有空气唦”。她说。
三舅娘是一位语言大师。她的方言灵机百变又带有某种幽默,古经轶事层出不穷。这被乡下人认为是一张“侉侉嘴”。但三舅娘也是一位劳动大师,她种黄瓜是一绝,比得上叠床架屋的森林,秋天满园垂挂的金色黄瓜像是辉煌的宫殿。她种的包包菜有脸盆那么大。她和我母亲一样会养猪,动不动四五百斤,肥到被老鼠咬缺了耳朵也懒得起身。
声明
来源:互联网
本文地址:http://farm.00-net.com/news/3n/2022-01-21/33687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