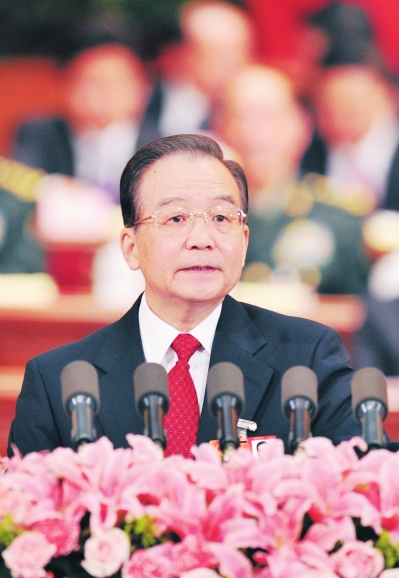新华网北京9月16日电(记者刘欢 李劲峰 沈洋)40岁的余彬是贵州省毕节地区赫章县水塘乡水潮村的乡村医生。在这个中国西南的贫困山区,他就是当地农民的“私人医生”。“出诊不分白天黑夜,夜里两三点被人叫醒去看病也是常有的事。”在余彬看来,乡村医生是农村全天候、廉价、好使的医生。
目前中国像余彬这样的乡村医生共有超过100万名。这些新时期的“赤脚医生”植根广大农村,承担着农村地区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在中国农村公共卫生服务网络体系中发挥着“网底”的重要作用。
“如果要去乡镇卫生院,坐车花钱不说,路上还得要近一个小时,有点急病还真不行。”江西省南昌县小蓝工业园沥山村村民张志和告诉记者,农民喜欢乡村医生,“是因为他们就在自己身边,看病价格还很公道。”
乡村医生这一中国特有的农村卫生队伍,大多由不脱产的村级卫生人员组成。这一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职业曾因“半农半医”的特点,而被农民亲切地称为“赤脚医生”。1985年后,经卫生部门考核达到医士水平的“赤脚医生”统一改称为“乡村医生”。
沥山村63岁的乡村医生张兴德就曾是一名“赤脚医生”。从医已经40多年的他,经历过学徒、“赤脚医生”、村卫生所医生、个体诊所负责人的多重身份转变,也品尝了中国乡村医生的酸甜苦辣。
他回忆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各个村里半路出家的“赤脚医生”并不少见。尽管当时村卫生所条件差、药品缺,但医生地位较高,挣得也不一定比别人少。“当时大家都是挣工分,成年男子不缺勤一年工分为4000分,而医生可以挣到4500分。”
数据显示,到1980年,中国“赤脚医生”总数达146万多人,平均每个生产大队有2.1人。依靠集体经济的支撑,农民只需花一小部分钱就能看上病、看好病。这一农村医疗救助体系为广大农民构筑起最基本的医疗保障,被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誉为“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健康收益”的“中国模式”。
这一体系持续了20多年,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逐渐呈现“网破、线断、人散”的局面。农村问题专家陈锡文分析其原因时指出,随着农村经济改革的实施,农民看病就医的性质由计划经济时代集体组织所提供的福利,变成自身消费行为;同时,大部分经济不发达的乡、村组织也不再能对合作医疗机构提供足够的资金,原先的乡、村医疗组织有的消亡了,有的由福利型转变为纯粹经营型。
1990年前后,当时的村主任找到张兴德,希望他办个人诊所,挂沥山村卫生所的牌子,承担村里的公共卫生防疫工作。“也就是说,我的个人诊所要承担原来村卫生所的公共职能,但村里一分钱不给。”张兴德说,因为对村民有益,即便村里没有投入,他也愿意做。
但更常出现的情况是,由于村医收入不高、社会保障差,村医岗位很少有人应聘,偏远地区的年轻村医纷纷改行外出打工,村医队伍结构日趋老龄化,陷入后继乏人的尴尬境地。不少地方农村甚至出现“设备全了、药价降了、医生没了”的局面,造成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网底”不牢。
针对这一状况,从中国国务院到地方政府,陆续出台多项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政策,以完善村医补偿机制,提高补助、改善待遇为切入口,全力以赴织牢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网底”,并将此项工作摆上全国正在开展的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的重要位置。
今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指导意见》出台,其中明确提出,健全多渠道补偿政策,根据乡村医生提供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多渠道予以补偿;确保2011年年底前每个应设村卫生室的行政村都有1所村卫生室,每个村卫生室都有乡村医生。
贵州省贵阳市息烽县流长乡前奔村卫生室的乡村医生罗孝华说,提高村医补助后,他估计今后每年行医收入能达到近两万元,“这个收入水平能和外出打工的工资收入基本持平,有利于吸收 新鲜血液 加入到村医队伍中来,逐步缓解队伍结构老化的问题。”
此外,不少地区还纷纷安排专项资金,用于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必备医疗器械配置和包括学历教育在内的村医业务培训,进一步改善村医从业的软硬件环境。
声明
来源:互联网
本文地址:http://farm.00-net.com/news/11/2011-09-16/15079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