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锦清——
“打捞”黄河边的中国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凤云

曹锦清(左)在乡村调研。
曹锦清,著名社会学家。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1986年在华东师范大学获硕士学位。曾任教于上海市城建学院,后为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著作有《现代西方人生哲学》《平等论》《中国单位现象研究》《黄河边的中国》《中国七问》《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合著)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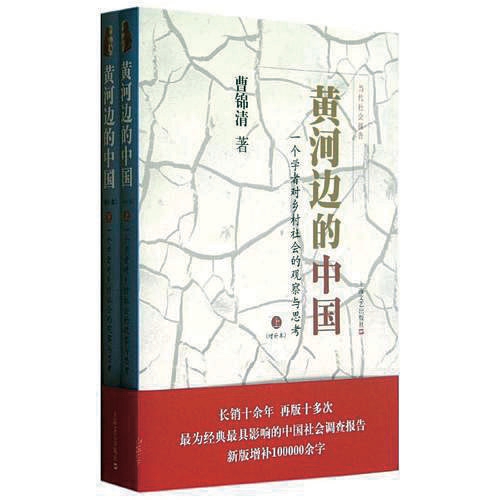


如何用我们的语言
来准确表达我们感知到的那些经验,
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问题。
我们在书房里坐下来,一把椅子一把沙发,看起来都有些年头了,沙发上铺了一块很耐磨的布,洗得干干净净的。房间不大,两面墙打了书柜,从上到下摞满了书。这是曹锦清教授女儿家的书房,书是绝对的主角,亦如他自己的家一样。
农历辛丑年岁末,春节前的一天,北京上空被一片厚厚的云层包裹着,正是忙年的时候,曹教授还是非常客气地抽出时间接受了采访。
作为中国现当代社会学界一个标志性的存在,曹锦清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背着背包走进河南乡村,历时4年写出了《黄河边的中国》这样一本关切中国现实的力作。甫一出版,犹如大洋彼岸那只蝴蝶的翅膀,掀起一股飓风,将整个社会的目光扭转了方向。中西部乡村,那里的人们,他们被改革大潮裹挟着的人生命运,终于被相对“完整”地看见了。
但是他并没有刻意地谈论过去。在接下来将近三个小时的采访中,老先生说得最多的是这正在研究的中国制度史。他说中国社会转型远未结束,时间的年轮依然穿行在“历史的三峡”当中,拉长时间段看,终极较量还是要归结到制度和文化上来,这对于认清国际国内形势尤为重要。
老先生已经年过七旬,依然关切着中国的当下和未来。而我们这次要探寻的,正是这种关切的由来。
一
故事可以从1988年讲起。
1988年,距离小平南巡还有几年,总体来说不是一个特别引人关注的年份。这一年,华东化工学院(华东理工大学前身)成立了一个文化研究所,进行现代社会转型研究。文化所分了四个组,一个研究农村社会,一个研究国企改革,一个研究小城镇,还有一个是各国文化比较,着眼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前提下进入到社会转型有什么共同点、不同点,尤其是发达国家早期社会转型。这在当时算是一个比较庞大的计划。
但是谁也没想到的是,到了1992年研究所内部首先开始了分化。一些人干脆“下海”经商去了,还有的研究因为种种原因而搁浅,只剩下农村组的两三个人,曹锦清就在这个组里面。
当时也有朋友劝他,说研究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重点得研究城市,因为工业化、现代化的中心在城市。曹锦清当然也清楚这一点,但还是觉得乡村更易于亲近,老百姓也欢迎大学教授到乡村去走一走、看一看,所以还是决定留在农村组。
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是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关键期,经济转型与社会分层几乎同时出现。在农村组的曹锦清关注到,1990年上海确定开放宗旨之后,沿海发展加速,农民工的流动也加速了。不计其数的农民从中西部尤其是沿黄一带潮涌般来到前沿开放城市,寻找出售劳动力的机会。这些洗脚上岸的农民意志是如此坚定,忍受着超强度的劳动,栖身在恶劣的条件下,似乎打定了主意不回乡村。
沿海开放城市正在大踏步奔向现代化的道路上,而沿着铁路线进城的数以万计的农民则徘徊在现代化的大门口,拎着蛇皮袋不断地往里张望。
逐渐地,工伤事故被频繁报道出来。因为操作机器不善而被切断了手臂;进入工厂之后身份证被统一收走;怕工人从厂子里偷东西出厂要例行搜身;工人挤在肮脏不堪的大通铺里,没有福利可言……
这对从事农村研究的曹锦清造成了很大冲击,时至今日说起来依然有些激动,“农民工是供大于求,而且是绝对剩余啊,就是资方对劳方的绝对的优势呀。”
绝对的优势意味着其中一方缺少制衡的能力,这是工伤事故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1993年11月,深圳市龙岗区葵涌镇的一家玩具厂发生了一场火灾,被视为那一时期一个代表性事件。这场大火烧掉了几十名打工妹鲜活的生命,其中绝大多数来自农村,这场大火触痛了社会的神经,也由此引发了更广泛层面的讨论。
为什么这些人前赴后继要到发达地区去?他们身后的家乡到底发生了什么?
“当时农村的问题已经被感知到了,尤其是农民负担问题,但是不系统,具体怎么样搞不清楚,这些信息被沿海的光芒遮蔽了。都是看着沿海发达,然后就是出国热,都关注这个东西,包括电视剧也是,农村的情况没有大规模见诸报道的,大规模视而不见。”曹锦清说,这是促使他后来去河南调查的一个直接动因。
与沿海开放地区相对的中西部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境况,在更大层面更具体问题上的认知滞后了。有人深陷在时代的洪流中无暇他顾,有人看到了更远更深刻的东西并试图一问究竟。曹锦清显然属于后者。
1996年5月的一个清晨,与前来送行的妻子话别后,曹锦清登上了开往河南的138次快车,向着中华文明发源地之一——开封市驶去。
他在当天的笔记中写到,“这次河南之行,仿佛有一种回归故里的感觉,我要亲临黄河,聆听她的千年倾诉。我要踏上这块古老的平原,看看至今仍然从事农耕的村民与村落。”
没人要求他这么做,甚至调研经费也是“化缘”化来的,他只是遵循着内心的召唤,做了据他说只是“一个研究者该做的事情”而已。
然而当我们梳理过往,就会发现这召唤由何而来。乡村在他人生中所占的分量太重了。黄河沿线这趟历时两年又风尘仆仆的调研,只是偶然中的必然罢了。
二
曹锦清的童年是在乡村度过的。
由于家庭变故,5岁那年曹锦清被送到了浙江龙游县的外婆家,一个叫做横路祝的小山村。于是寒来暑往,秋收冬藏,跟着大人砍柴喂猪,看着村民夯土垒墙。10岁那年龙游乡村闹饥荒,吃不饱饭,外婆给母亲写信,这才辗转来到上海。
乡村的这段生活经历,不能不影响到他长大后的观察视角和研究方向。
初到上海是1958年,一家人住在南市区的老房子里。那时候的南市区密布着工厂,人们早起晚归到工厂里做工,日复一日。初到大城市的曹锦清并没有感到新奇,反而觉得机械单调,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
后来家里增配了一间5.8平方米的亭子间,这个下有三家合用的灶间、上有晒台的亭子间就变成了少年的卧室和书房。曹锦清在墙上贴上用毛笔写的“为谁活,怎样活”六个大字,一位少年探索人生意义的历程开始了。
他读遍了学校里能够找到的有关人生意义的青年修养书籍,高一那年突然又觉得人生的意义可能深藏在浩瀚的星空中,于是买了《天文学教程》和一些旧天文学杂志,磨制镜片,自制望远镜,苦苦求索,始终找不到答案。
还是乡村给了他一点启发。
有一年他回龙游,满脑子装的也是这样的问题,于是问他的外婆,人活着到底为什么?外婆说,“孩子呀,人活着不就是让乡邻乡亲说你是个好人吗?”
外婆懂点医术,十里八乡的孩子生病了经常会抱来给她看。外婆摸摸头,烧炷香,临走再包些中草药,小孩的病很快就能好。曹锦清知道外婆给乡村的孩子看病从不收钱。
但这显然不足以解答少年心中的困惑,他又去问已有四个孩子、累得未老先衰的表姐,人活着有什么意思?表姐说人活着根本没什么意思。
他又拿同样的问题问全村人公认的最能干的大舅妈,她说“傻孩子我告诉你,只吃不做是猪种,只做不吃是牛种,做做吃吃是人种。人嘛,就是干活吃饭两件大事。”
他问一向沉默寡言的老外公,外公正在屋后大樟树下劈柴,听了他的发问放下柴刀,眯着眼看了好一会儿,一言未发又去劈他的柴了。
“这些场景如今说起来历历在目,你说他们的回答哪个是真理?很久以来我才不得不承认实证主义的说法,人生意义一类问题属于价值判断而非事实判断,价值判断是不能通过事实判断得到证实或证伪的。”曹锦清说。
南市区每天的生活都是从拉粪车的吆喝声开始的,大人们要工作,学生们要上学。到了晚上,曹锦清就回到属于自己的亭子间里,格外想念有外婆和伙伴的乡村生活。
可是到了1968年,高中毕业后的曹锦清来到崇明岛的红星农场插队,本来怀念着乡村的他却发现那也不是他想要的生活。直到四十岁那年,也就是文化所成立的那一年,曹锦清读到了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其中的一个观点对他触动很大。即当一个社会的各个阶层尤其是底层阶层的头脑都提出“人为什么活着”的问题时,表明社会结构已经发生重大转变,各社会阶层都先后越出原有的生活常轨而置身于一个全然陌生的社会环境之内,故而发生“人为什么活着”或“生活意义在哪里”这一令人焦虑的永无终极答案的大问题。当社会生活沿着原有常轨进行的时候,传统的习俗、风尚、教育等等已经规定了生活的意义,已经解决了“为什么而生活”以及“怎样生活”这两大问题。所以,人生意义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社会问题。
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恰巧就处于这样一个社会结构重大转变的阶段。有人一夜暴富,有人则挣扎在贫困的边缘,贫富差距拉大,原本平平的社会结构极速瓦解。物质上看起来比起之前好太多了,但是普遍的感觉是活得挺累,活得空虚。所以后来有了围绕潘晓提出的“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这样的问题展开的社会层面的大讨论。
为了对抗这种经济转轨带来的精神层面的虚无,很多方面想了很多办法,比如开展老一辈讲述当年人生理想的活动,追问他们年轻时的奉献到底为的是什么,以期给年轻一代以精神上的指引。当时上海还树立了一个典型,讲的是下岗女工查文红在穷乡僻壤义务任教的事。其中查文红有一句话,说的是“我是为孩子们来的,在这里我感到活得很有价值,这就够了”,很能与当时年轻一代普遍找不到人生价值的状况相对应。
也就是那个时候,曹锦清开始重新认识自己,放下“人生意义”这样形而上的问题去关注现实。了解这个变动的社会实在是太重要了,曹锦清开始了从哲学研究向实证主义社会学的转向,并且在文化所四个组里选择了相对偏门的农村社会研究这个方向。
而这些,都成了后来那趟著名的黄河边之行的细微铺垫。
三
1996年5月12日清晨,138次列车很快驶离了躁动现代的大上海,驶入广阔古老的乡村。一个中年学者带着他的疑问和关切,随着隆隆的车轮声,慢慢浸没在早晨太阳的光晕里。窗外景物飞逝,一切都是看似熟悉而又未知的,他要探寻的就是这熟悉当中的未知。
相较于改革前沿的大上海,20世纪90年代末的河南乡村还处于一种前现代的势能当中。即便如曹锦清所认识到的乡村具有相对于城市更大的包容性,熟人社会的组织结构也不允许一个陌生人轻易入场。作为一个南方来的学者,人生地不熟,为了能够顺利进入乡村颇费周折。最后还是通过河南大学的朋友取得了一张进入乡村的入场券。
5月30日,进入兰考县小靳庄。兰考是60年代中期焦裕禄工作过的地方。30年过去了,茫茫盐碱地、风沙地不见了,放眼望去是一望无际、行将开镰的小麦和纵横交错的阡陌沟渠。所有村子都掩映在绿树丛里,那是焦裕禄提倡种植的泡桐。
“到小靳庄老李家时,已经晚上8点,站在大门口的老李妻子,看上去眼熟,像我老家的表嫂。老李3个孩子,大女儿已结婚,小儿子读初三。大儿子和女朋友在复习功课,准备高考。后来他们告诉我,那温柔的女孩是河南大学某教授的女儿,两个人正做着金榜题名的梦呢!”曹锦清带着感情记录下了当时的情景。
他就住在老李家,在这之后的两年时间里,他在河南乡村奔走,经常就住在像老李这样的农民家里。“化缘”化来的那点经费,有一部分就给了这些农民,看着穷一点的就多给一点,富一点的就少给一点,用在自己身上的就是最最基本的开销。
沿路村庄几乎一切有墙的地方都刷着“大跨度,超常规,争一流”“谁致富,谁光荣;谁贫穷,谁无能”这样的标语;肮脏、破旧的公共汽车挤满了风尘仆仆的农民,奔驰在乡间公路上;尚未脱贫的人们兴致勃勃又精打细算地购买着廉价劣质的工业品;用打工挣来的钱苦苦支撑孩子教育费用的愁容满面的父亲;在“富民工程”口号下强行上马的村办面粉厂……
“在西方与城市高消费文化强烈刺激下,被激发出来的无限欲望正从城市蔓延到乡村。”每结束一天的调研,曹锦清就在笔记中详细记下所见所闻所想。后来这些夹叙夹议的文字原汁原味地保留在了《黄河岸边的中国》这本著述里。
显然,多年来按照某种规则运转着的乡村传统秩序,在内外力的冲击下被打破了。虽然不及沿海发达地区对于财富积累的疯狂,躁动不安和生怕被落下的恐惧是一样的,一向“知足常乐”又慢节奏的村舍概无例外卷入到了对财富的崇拜和攀比中。
“的确,穷有穷病,富有富病,与穷病、富病比,穷还急着富的病更可怕。在调查中,一位基层干部对我说,在生产力低下的中部农村,要用三五年或八九年时间赶上东部沿海地区,是不切实际的。”
地方政府急于迎头赶上的急迫和焦虑显露无疑,迅速富起来的愿望与可以迅速富起来的条件之间形成了巨大的鸿沟,在某些局部变得扭曲。
对于一些地方官员与农民共同防忌的问题,曹锦清就只能仔细观察,晚上回到小旅馆或者农民腾出来的空房间,再赶紧拿出本子记下来,并附上自己的思考和解读。
不忌讳的情况下,他也会拿出笔记本和农民们算算收入支出的明细账。看到算出的结果,农民们都很吃惊。而曹锦清对于这种吃惊本身感到吃惊,因为他发现,即便是曾经上过高中的农民,也从来没想过像一个企业主一样去关心种地的投入和产出问题。
地点一个一个累积,资料一步一步丰满,转型中的中原乡村社会,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后的农民与土地、与市场、与社会、与政府关系的变化……就像拼图一样,一块块珍贵的碎片被捡拾起来,关联起来,一个改革开放后中部乡村的真实图景逐渐清晰完整起来。
2000年,《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出版,旋即销售一空。此后连续再版十余次,累计发行超过5万册,成为当代中国社会调查报告类最畅销的书籍。
书是2000年12月出版的,2001年3月份北京召开全国两会,有代表就是拿着这本书呼吁国家重视三农问题,重视在东部沿海开放城市高速发展对照下的中西部乡村的现实状况。
但是曹锦清并不认为这是他的功劳,他曾用“一石激起千层浪”来给予解答。
“石头与千层浪到底是什么关系呢?是不是单线因果关联呢?”他说不是,如果同样的石头扔进草丛里,只有几棵小草摆动几下便悄无声息了。扔进早已起浪的江河湖海更是没有影响。恰巧扔进平静的水塘,于是起了千层浪。
“这是石头之功还是水之功呢?我说石头只是个外因,内因在水本身。”曹锦清说。
四
这份调查报告一开始并没有打算发表,原本是作为内部读物进行印刷的。曹锦清因此被请到出版社进行文稿校对。大概进行了一天的时间,他早上去的时候几个工作人员齐刷刷地站起来迎接,他也没有太在意。校对完准备离开的时候,工作人员又站起来示以同样的尊重。曹锦清心里也打鼓,不知道这样一份报告会有怎样的影响,当时又不方便问。
“后来呢?”我问。
“后来就有一个人送我到门口,然后站住了,握了一下我的手,非常郑重地跟我说,‘曹老师,谢谢你。’”曹锦清说他这个人不轻易动感情的,那个时候眼泪差一点掉下来。
当然,这本书的写作方式也引起学术界的一些争议,学术理论与报告文学是不是没有区别了呢?人们提出疑问。
曹锦清也因此苦恼了很长时间。他说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都得处理两对关系,一是人的主观性与外部世界客观性之间的矛盾;二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人的社会行为是一种可以观察到的社会事实,人赋予自身行为的主观意义对研究者来说,是另一类更重要的社会事实。
“关于一般与个别,科学与人文处理的方法是有区别的,我把科学的方法概括为‘通过个别而获得一般’,如在自由落体公式h=1/2gt2中,研究者、个别实验及实验过程都不存在了。我把人文方法概括为‘在个别中直接呈现一般’,这种直接呈现一般的个别,我称之为典型。”
为了寻求典型的一般性,曹锦清尽可能将调查范围扩大,东西南北中都去跑一跑看一看。对不同地方的不同农户、村庄和乡镇的三级调查中也经常问类似的问题,写在书里便给读者以重复的感觉。出版社的编辑曾建议他把重复内容删掉,但是他想用这种表面上的重复弥补此类表达方式的内在缺陷,用不同区域同类调查结果的一致性解决“通过具体案例直接呈现一般”这一难题。
据说,曾经据费孝通的学生讲,费老晚年一直自我检讨,说自己那么多年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社会生态,而没有去重点关注社会心态。而这个问题,曹锦清在中原调查的时候,已经把社会心态放在了重要的位置。
在《黄河边的中国》出版后的一次访谈中,曹锦清是这样说的:
“人们对事实的主观判断特别重要。官员看到了经济增长,也看到了老百姓由于工业发展就业比过去好了,老百姓的钱确实比过去多了,房子也盖得比过去好了,他就以为天下太平了,他以为只要把GDP搞上去,把老百姓的收入搞上去,其它的问题就都解决了。这也是我们三十年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主流想法。但是老百姓收入增加和老百姓对自己生存处境的判断是两码事。所以,在研究社会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社会心态——人们对自己的生存处境、对周边的环境、对财富权力的主观判断,这个主观判断是一个客观事实。这种主观判断是形成群体性事件的一个主要原因,单把社会事实看成是可以量化的、可以观察的是不够的。”
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曹锦清和同事去浙北乡村调查就觉得遗漏了些什么,后来他总结是把活生生的具体的人抽象化、数字化、概念化了。“在社会研究当中,人们的情绪、意愿、希望、评价,即人的主观方面,或者说普遍的社会心理是一个重要的社会事实,这是黄河边的调查得出的很重要的一个结论。”他觉得普通民众的社会心理有权也应该得到表达。
而且曹锦清相信,一个民族的日常语言能够表达自己最精髓的思想以及这个时代最想表达的东西。他不主张用那些晦涩的翻译语言来进行表达。“如何用我们的语言来准确表达我们感知到的那些经验,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问题。”
进入河南之后,曹锦清碰到坐在“陈桥兵变”纪念馆门槛上的一位老汉。
“现在过得咋样?”
“好哇,我现在做不了主了。”
曹锦清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旁边一位中年农民就充当了翻译:
“他说他的儿子媳妇不听他的话。”
一句直接引语直截了当又活灵活现地反映出了一位农村老人的处境和普遍心态。
“当然,你要判定哪些语言能够非常经典地反映出这个事情,要有识别力。你为什么把他那个语言记下来?因为你赋予它了一般意义。”他说这一点上调查研究就和捡垃圾差不多,“不是叫你把垃圾箱背到家里来。那里面的废铁可以卖钱的你拿来,越能卖钱的你越要关注,要从很多纷繁复杂的现象当中捡出你的东西来。”
版权声明:本文系农民日报原创内容,未经授权,禁止转载。任何单位或个人转载,请致电010-84395265或回复微信公众号“农民日报 ID:farmersdaily”获得授权,转载时务必标明来源及作者。如有侵权,本报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公众号“零度往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