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走过的乡村
高洪波

高洪波,1951年出生,内蒙古开鲁县人。儿童文学作家、诗人、散文家。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七、八、九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先后出版过《大象法官》《吃石头的鳄鱼》《我喜欢你,狐狸》等20余部儿童诗集;《高洪波军旅散文选》《墨趣与砚韵》等30余部散文随笔集;《鸟石的秘密》等20余部幼儿童话;《鹅背驮着的童话——中外儿童文学管窥》《说给缪斯的情话》等评论集以及诗集《心帆》《诗歌的荣光》《诗雨江南》等。2009年出版《高洪波文集》(八卷本),2018年出版《高洪波文存》(九卷本)。曾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庄重文文学奖、冰心奖、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等奖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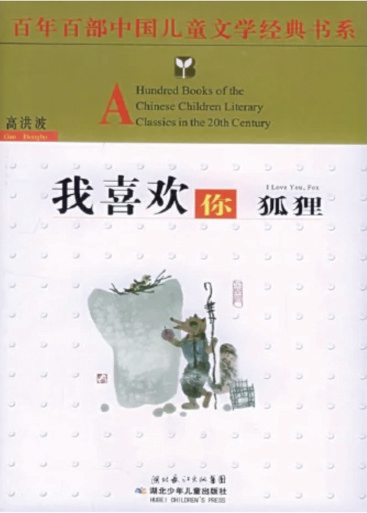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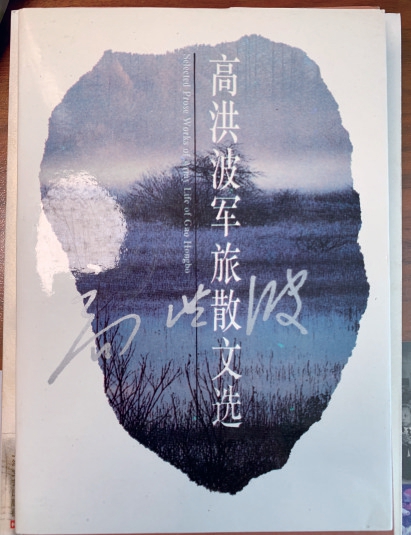
乡村的记忆是童年和青春混合的记忆,
但是我所讲到的高党和龙港现代化的乡村记忆,
我个人认为,是中国复兴蓝图的未来展示。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中国人拥有乡村记忆的百分比应该非常高,哪怕你是拥有北京、上海、天津、沈阳等大城市户口的人。如果往上查三代,可能你们身上都有乡村前辈的田野基因,更何况“老三届”一代人。比如我辈,大多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即便没有上山下乡,像我这样从中学直接入伍的军人,除了军营记忆之外,其实乡村记忆依然很多。因为军营所在地大多都在山乡,同时军营中的伙伴又绝大多数是农家子弟,听他们讲述故乡的生活就补充了我的乡村记忆。
故乡的田野
故乡的田野,其实也可以称之为科尔沁的草原。我虽然生活在一座草原的县城里,可是我乡下的亲戚很多。外祖父住在乡下,离城只有三公里,几个姑姑住在更远的乡下,这两处都是我假期经常要去的地方,所以我的乡村记忆往往伴随着表兄、表弟、表姐、表妹的身影。
故乡的田野在我的记忆中,夏天是青纱帐,高粱和玉米遮蔽着平坦的草原。故乡还有沙沼地带,这些地带上绝不仅仅是沙漠,有生长扎根很深的甘草。它们把碧绿的叶子放肆地伸在阳光下,很容易被人辨识出来,然后它们会被连根挖起,成为一味不可或缺的有名的药材。此外,这些沙沼上生长着马莲花,马莲的叶子非常结实,几乎可以当作绳子使用,马莲的花开得漂亮,蓝幽幽的,给人一种蓝天上坠落的碎片一样的感觉。
所以,我的乡村记忆是外祖父家的菜园子,是田野上和表弟们捉蝈蝈的快乐嬉闹,还有乡下马车颠簸的道路,在驮干草的马车上舒适地躺着仰望蓝天的感觉,尤其奇特,因为这个场景让我想起契诃夫笔下的《草原》,而马车上的干草垛柔软舒适,在有节奏的摇晃中,有催眠的特殊功能。故乡的马车一般都是胶皮轱辘,跑起来轻快利索。赶马车的人在故乡都叫“车老板子”,也同样利索,甚至有几分彪悍,一根长长的鞭子在手,随着一声脆响“驾”,马车就噔噔噔地跑向前去,在乡间的道路上扬起一片灰尘。
我十三岁上离开内蒙古草原,后来平均三五年便回归故乡一次,回归故乡不为别的,只为去给我埋在故乡的老奶奶的坟前烧几张纸。老奶奶的坟在一片茂密的树林里,坟上有一人多高的青青的芦苇。从田间小道到奶奶的坟前要穿过一片同样茂密的,甚至让你感到拥挤的向日葵方阵,向日葵们擎着骄傲的葵花盘,用带刺的叶子阻扰着你的进入,那一刻你觉得梵高笔下的向日葵都不足以表现我故乡奶奶坟墓前那片巨大的向日葵方阵。金黄色的向日葵、碧绿的芦苇,还有高大的杨树,这都是故乡田野留给我的意象,说印象,当然也可以。
故乡的小河、小水渠、小小的沼泽地都曾留下过我的脚印,一个北方少年在北方的夏天里放肆地撒着欢,或者和小兄弟们一起匍匐在瓜园的垄头里,去窃取甜蜜的西瓜。虽然有被看瓜人当场捕获的危险,但是我们乐此不疲,这一切都是故乡田野给予我的珍贵纪念。
贵州的杨柳村
十三岁上,我和全家一起从内蒙古的故乡迁徙到了西南的贵州。在贵州的两年间,我住过三处县城,一处毕节,一处黔西,还有一处都匀。毕节和黔西是我学会游泳的地方,但是和农村没有更多的交织,唯独在都匀,我有幸到了一个小村子,这个小村有个美丽的名字:杨柳村。那时我们以中学生的身份进行一个月的助民劳动。
杨柳村傍着一架彩虹般的铁路高桥,小村从而显得更小,杨柳村不富裕,但也不算贫穷。我们散住在农民家里,房东们的客房里、客厅里普遍供奉着“天地君亲师”的牌位,这五个字所包含的意义,当时在我的眼里,仅只是五个字而已,其实这里边有汉文化的精华和传统所在。
在杨柳村,我学会了插秧,也学会了担粪走过溜滑的田埂,更学会了面对蚂蟥的偷袭、猛击一掌将其震落的绝招。蚂蟥都是水蚂蟥,不同于我后来从军在云南时见到的特别厉害的旱蚂蟥,但是水蚂蟥如一片柳叶般大,一旦被它吸住,血会流淌不止。而杨柳村的稻田里,这种水蚂蟥特别多,它们静静地潜伏在秧田里,等待着一双双赤脚落在水里之后,它们迅速吸附过来,不知不觉地吸去了你的鲜血,伤口还无法止住血,大概它有一种特殊的毒素,是让血液不能及时凝固的原因吧。因此蚂蟥在我看来,它的讨厌、它的无情甚至超过世上所有凶猛的动物,其实它不过是一个昆虫而已。对付蚂蟥,农民们的绝招是在它吸血的上方猛击一掌把它震落,然而我常常震不落腿上的蚂蟥。此时此刻你须用钢笔里的墨水滴在蚂蟥身上,一滴它的身体顿时变蓝,然后迅速蜷缩在一起,很狼狈地离开了你的腿部,掉在地上。当然对付蚂蟥最好的办法是用一撮盐撒在它的身上,这也会使它很快受到重创。
在与蚂蟥的斗争中,我知道了南方农民种水田的艰辛,在插秧的时候,也感受到了水稻这种植物对南方农村的特殊意义。当然不只是水稻,我们还要和农民一起种苞谷。在种苞谷的时候,那是在山峦上,我和同学们意外地发现了一眼甘泉,这泉水从一丛绿草下汩汩涌出,泻出一串串晶莹的气泡,喝一口,甜丝丝的,好像有人放了糖!这应该是我平生喝到最奇特、最甘美的山泉,现在不知道它被人开发出来没有,那水质肯定不逊于现在所有大品牌的矿泉水。
我至今不明白这泉水的成分是什么。后来我饮过各地的泉水,无论是崂山矿泉还是虎跑泉,甚至号称“天下第一汤”的昆明温泉,那滋味距杨柳村小山中的泉水,总差着一大截。是啊,也许它仍然寂寞地淌在山野间,“养在深山无人识”,但无论如何,泉水就是泉水,它是大地母亲赠与我们人类的乳汁,滋润着禾苗、小草,也滋养着小鸟、小兽。只要是泉水,就不会被废弃。我相信这一点。
从四季青到坨里
我的乡村记忆随着家庭的迁徙从贵州来到了北京。
在北京,我们以中学生的身份又参加过无数次的助民劳动。我记得我们在夏天住过北京“四季青”公社,同学们住在小学校的课堂里,地上铺着炕席,大家把铺盖放上之后,一个班的男生欢乐地在铺上嬉笑打闹,我甚至和一个同学立马摔起跤来,一如快乐的夏游或者秋游。在“四季青”的日子里,我们一帮男生在傍晚的时候到田野上追逐,有一个男同学跑在前面,但是他突然身体矮下去,只露出一个头颅,我们围过去一看,他不小心踏入了一个表面干涸的粪坑。那一刻苍蝇飞舞,众声喧哗,但毕竟同学情深,我们七手八脚找到工具,让这个倒霉的伙伴从粪坑里脱身,然后在一边用清水狼狈而尽情地冲洗自己。“四季青”的房东是一对老夫妻,对我们呵护有加,我们出去捉青蛙,他还为我们烹饪,味道好极了。我们还去铁路上追火车,为田野施肥,也帮助农民们拔草,一系列简单又轻易的农活让我们这些半大孩子们快乐地操作着,所以“四季青”的夏天,滋味无穷。
“四季青”的日子结束之后,秋天了,我记得我们到了北京房山县的坨里。我们住在坨里的村子里,被一座古塔所吸引,同学们经常围着古塔看麻雀们飞舞,用手中的弹弓击打这些小生命。也是在坨里,一个调皮的男同学捉住一条小蛇,悄悄放在班主任女老师的饭盒里,女老师打开饭盒,被当场吓得昏倒。顽皮的学生岁月和坨里秋天美丽的景色,以及坨里的柿子树、坨里的红薯、坨里的各种山果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特殊的滋味。
我们主要的工作是收红薯,每天去红薯地里挖红薯,然后把红薯捡到筐里,分头带回村里。我们的主食也是红薯,房东给我们做的红薯花样很多,不光是蒸红薯,还把红薯擦成丝,做成红薯粥,还有红薯干。吃红薯吃到最后,胃里直反酸。改善生活的时候就是一顿金黄的玉米面窝头,窝头就着老咸菜,我们这帮中学生们吃得喷喷香。
所以那一年坨里的秋天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乡村记忆,而且我们是步行从长辛店的火车站走到坨里的村子里,大家背着行李,十几里的路程把我们累得够呛。
大约十年前吧,我学习驾驶汽车的时候,曾在房山的一个汽车部队住过一天。期间,我曾到坨里去寻找那昔日的小山村感觉,但是少年时期的记忆已经被现实涂改得面目全非。坨里的城镇化建设十分彻底,我企图寻找那目标显著的古塔,旁边的乡亲们告诉我,那古塔早就已经坍塌了。坍塌的古塔却拥有我矗立鲜明的记忆,我现在能写下怀念坨里秋天的文字,就是一个例证。
云南的村寨
从军的时候,我的驻地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大荒田。“大荒田”三个字肯定是属于乡村记忆的特殊板块,周围的村庄是我们经常出没的地方。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我曾经带着一批新兵驻在周围的村庄,一驻就是一个月,我对新兵进行培训的时候也和乡村的房东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当时正是冬日,雨雪霏霏。于是每天晚上好客的房东便燃起一盆炭火,沏得一罐烤茶,同时端来葵花子和花生米,我和我的小新兵们坐在火塘边,有一搭没一搭地烤火、聊天。聊天,云南叫“吹牛”,这里的“吹牛”和北方的意义不一样,丝毫不带贬义。
吹牛的内容很广、很宽,也很泛,因为这些年轻的军人来自地北天南,比如我从北京来,有一个班长家在昆明,还有一个战士来自遥远的哀牢山上的苦聪山寨。所以房东夫妇很高兴,而且他们的两个小儿子更高兴,在他们眼中,我们这一群南腔北调的解放军军人,是最有趣的人。
云南的农民说起话来,却文雅之至。譬如说某一项活动令人玩得痛快,舒坦,它必定用一个词来形容,叫“安逸”。又如火塘上的火不旺,需要重新点火,北方人就说“火着了吗”,而房东则用一个字“燃”,“火燃了”。一个“燃”字,显出了文化素养。此外,“晚上”这个词,房东换以“夜间”;“吃饭”“开饭”,他用“请饭”来表达一种特殊的情义,这些云南乡村所带来的中国古文化的熏陶让我感到非常惊讶。
这村子距我的大荒田军营十几公里,沿南盘江而形成一座颇具规模的大村子。房东的祖先们,都是屯垦戍边的军卒,聊起天来,他们都以故乡而自豪,而他们的故乡一律叫做“南京柳树湾高石坎”,我想这应该是明初大规模移民屯垦边疆时一个重要的集散地吧,很像山西洪洞县内的“大槐树”一样。北方洪洞县的“大槐树”是无数北方人故乡的象征,“寻根”一律以此为凭。由此看来,“南京柳树湾高石坎”给予滇中乡村父老的记忆,应该是与“大槐树”属同一类的意象。
当初那些戍边的军卒们驻扎此地时,肯定有一番拓荒之苦的。而后他们娶妻生子,将刀枪换为锄犁,慢慢地竟繁衍出这么多的村寨来,真是始料所不及。房东告诉我说,这四围山上,曾有过莽莽的森林,在他小时候,还知道有豹子出没于村口,蟒蛇盘踞于江岸,还见过豺狗和麂子。
说这话时,正值大雪纷飞,掩住了四周光秃秃的山峦,现在的场景是林木稀疏,昏鸦都很少见了。房东的两个小儿子听着父亲讲述童年的见闻,也觉得新鲜。父亲小时候所见到的这些动物,他们大概只能在动物园见到了吧。
雪一落,春节也追了上来。我们驻在村子里,和农民们度过那古朴的特殊的中国节日。
村中过春节,众多礼俗都一一免去了。但只留下一项,这是北方绝对少见的一项:以绿松毛铺地。
那个时节,不管你到村子里哪一家走访,一步踏入堂屋,必定满眼生绿。脚下是碧绿得发亮的新鲜松毛,就像大城市豪华人家铺上的绿色的地毯,踩上去软软的、滑滑的,略一呼吸,便有松香味儿沁入肺腑,让你精神为之一振。在这绿客厅上走动,给人一种踏入春天、走进森林的感觉,春的气息包围着你,绿的氛围挟裹着你,使你具体而又切实地感受到“春节”两个字,春天的意蕴。我度过很多很多个春节了,但是只有在这个云南小村寨中领着新兵战友们度过的春节,记忆碧绿中有些许暖意,这可能是一种“踏青”的风俗吧。
云南的村寨很多,我后来走过撒尼山寨,住过苦聪山寨,也到过傣寨、景颇寨,这些少数民族的村庄,有的以硕大的菠萝蜜款待过我,有的用香甜的红荔枝招待过我,还有村寨上的长者们背倚牛头,跟我合影的同时,顺便讲述过古老村寨的历史,这是在著名的佤族翁丁山寨。
云南的少数民族众多,不同民族有不同的风俗,但是他们毫无例外地都属于我乡村记忆的一部分。
龙港的乡村
我的乡村记忆中有很多来自带领作家乡村采风的特殊感受,比如在江苏睢宁有一个村叫高党村,这个村子专产甜酱油。乡村建设得很好,旁边竖着大标语:“高举红旗跟党走。”这个大标语把“高党”这个村名都镶嵌了进去,由此我感觉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在建设过程中对执政党一种深厚的情感。村子建设得很漂亮,而更漂亮的是我在浙江温州龙港市的一次乡村采访。
龙港是中国最年轻的一座城市,原来号称“农民城”,它的年龄在我采访的时候刚满一周岁。刚满一周岁的龙港市有一系列非常精彩的举动,它有印刷博物馆,有一批著名的乡贤纪念馆,比如著名诗人谢云的故居就在龙港。
龙港在我们到达的时候正好遇上了台风,沿海城市对台风的警戒度是我第一次看到。陪同我们的公务员们都说要昼夜值班,警惕大自然不请自来的暴怒。也就是这次走访龙港,我意外地发现龙港的乡村居然有智能垃圾箱。北京城市里,包括我所居住的小区,都有垃圾分类的标识,垃圾箱一般都分成三类,有的可以回收,有的不可以回收,还有厨余垃圾。但是在龙港,在这海边的乡村,我看到了好多座智能垃圾箱,当你把可以回收的物品投放进去之后,它会给你奖励,奖励有可能是一块肥皂,有可能是一包餐巾纸,还有可能是其他生活用品。这种智能垃圾箱的设置和对投放垃圾人的特殊的物质诱惑,或者说激励也行,使我看到了中国一个另类的、现代化的、与众不同的乡村。
在我的乡村记忆中,这一幕充满现代意义,也可以说是终生难忘。年轻的由农民城转变为城市的龙港,到今年也刚刚三岁。三岁的龙港,那昔日的鱼米之乡,那有诸多乡贤故事的富庶的地方,留给我一个非常特别的乡村记忆是寄托在智能垃圾箱上。我觉得这一个杰出的构想如果从乡村移植到中国的任何大城市,都将为中国的垃圾治理提供一个极具特色的成功范例。这样的乡村不再是破败、颓唐、荒凉,而是充满着现代气息和勃勃生机,也许这样的乡村是中国乃至世界乡村的未来,我希望中国的社会主义农村建设越做越好,城乡差别的沟壑逐渐被现代化的手段填满。因此拥有骄傲的城市户口的人们,比如我和我的亲人们,对乡村、对乡村记忆会有一种特殊的时代跃进,这个跃进寄存在江苏小村高党,也显现在温州龙港的村镇。
所以我说,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每个中国人都有一份难得的乡村记忆,它可能是你童年味蕾的记忆、美食的记忆以及对长辈温馨的怀念,也可能是你青春无悔的岁月的记忆,一如我很多“老三届”朋友们经历过的上山下山,或在云南、东北的建设兵团,或在陕西、海南等天南地北的山村里。乡村的记忆是童年和青春混合的记忆,但是我所讲到的高党和龙港现代化的乡村记忆,我个人认为,是中国复兴蓝图的未来展示。我希望这种现代化的乡村记忆一步一步拓展蔓延开去,因为它甚至可以引领一座城市的管理、一座城市的垃圾处理与现代化的治理模式。
乡村是中国的乡村,城市和乡村之间应该是互补的、互惠的,甚至也是互为师长的。没有中国的乡村,就没有中国的现实和未来,因为中国的乡村代表着民族、历史以及珍贵的土地。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是大诗人艾青先生的名句,也是我对乡村最大的感受。
版权声明:本文系农民日报原创内容,未经授权,禁止转载。任何单位或个人转载,请致电010-84395265或回复微信公众号“农民日报 ID:farmersdaily”获得授权,转载时务必标明来源及作者。如有侵权,本报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公众号“零度往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