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永不停顿的追求致敬
叶兆言 口述

叶兆言,1957年出生,南京人。1974年高中毕业后进工厂当了四年钳工。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1986年获硕士学位。八十年代初期开始文学创作,主要作品有三卷本短篇小说编年《雪地传说》《左轮三五七》《我们去找一盏灯》以及八卷本中篇小说系列,另有长篇小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花煞》《别人的爱情》《没有玻璃的花房》《我们的心多么顽固》《苏珊的微笑》《很久以来》《刻骨铭心》,散文集《流浪之夜》《旧影秦淮》《杂花生树》《陈旧人物》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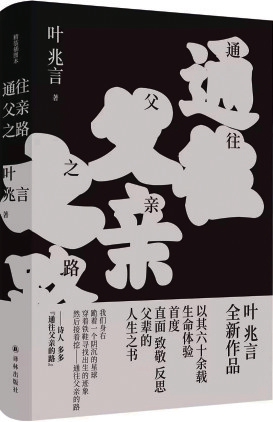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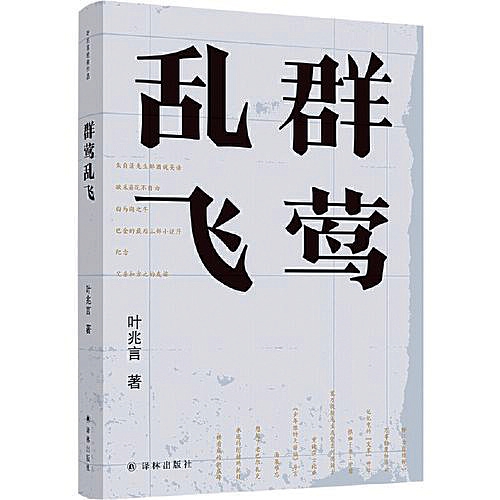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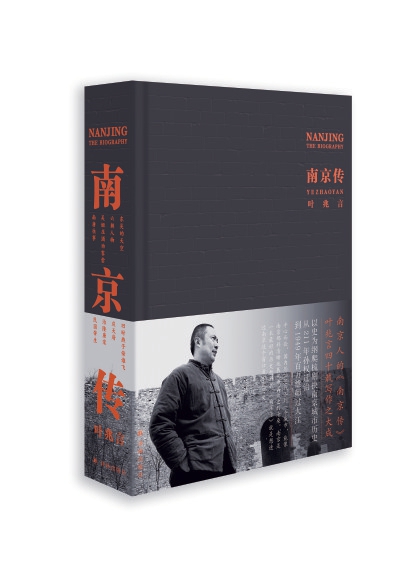

对于一个人来说,
最珍贵的倒不一定是年轻的时光,
而是无论到了什么时候,
他没有放弃追求的精神。
我就觉得不放弃的人生永远是优美的。
一
说起来,农村留给我的印象也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算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比较特殊时期的农村。那时候,农民没有城市户口,也没有粮票,这就决定了当时农民的身份,以及他们和城市人完全不一样的命运。
我对这一点体会很深。小的时候,由于父母的原因,我作为一个城市的孩子,在那个特殊时期,在江阴的农村待了差不多三年时间。我的母亲从农村进入城市,她的两个妹妹,也就是我的两个姨妈,她们在1949年以前也都到上海去做了工人。
农民进城,这段时期的城市化其实是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件事。那时候农民进城之后的选择也和今天特别像,他们都是想要进城去寻求一种更好的生活。
因为没有城市户口,我的二姨妈就在解放初期从城市回到农村结婚了。之后因为生孩子,暂时没有回到城里去,她就成为了一个农民。而我的另一个姨妈就成了一个上海的工人,她的生活就是完全城市化的。
她们进了同一个工厂,做同样的工人,只是一个回乡结婚,一个没有回乡,这个选择就造成了两个姨妈完全不一样的命运。可以说,就是当时的这种特殊时期的政策和做法,造成了当时农村和城市极大的分割。
现在的“80后”“90后”可能没办法理解这个事情。当下,农村和城市之间的流动变得很简单、很方便。但那个时期,城乡之间是基本无法流动的。
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我们在写作的时候,都喜欢歌颂农民怎么好、怎么淳朴,把农民这个群体理想化。但是另外一方面,起码在我们那个时代,所有农民的共同愿望,就是希望能变成城市人,渴望拥有粮票,谁也不愿意当农民。
我在江阴待了三年。刚去的时候,我只是个10岁的小孩。见到农村的瓦房里还围着猪圈,晚上没有电,只能点煤油灯,还有村里老人为自己预留的棺材,就放在屋子里……我一下就傻掉了,这就是我童年对乡村最深的印象。
那时候的江阴和现在不一样,真的非常穷,一年四季很少有荤菜,整个乡村仿佛沉浸在昏睡中。
三年的乡村生活让我也改变了很多。在江阴农村,夏天一般是在河里洗澡,冬天可能就不洗澡,或者最多到城里去洗一次。记得那时候在村子里,会烧一大锅开水,然后全村男女老少大家轮流就在大锅里洗一洗。当时的我稀里糊涂,也不知道怎么过来的,但是能够感觉到,自己已经完全适应了那样一种绝对乡村化的生活,所以很正常地就有了一种乡村性的眼光。记得有一次我们学校组织去江阴县城参加运动会。说是参加,实际上也轮不到我们参加比赛,就是去看的,那时候对我来说很新鲜。
对一个孩子来说,三年可以有很大的改变。到了夏天,农村的孩子都是打赤脚,这个习惯也被我带到城市里。我甚至能够光脚走到南京最热闹的街上去。到现在,我还经常喜欢在家里光着脚。
后来我也多次回到故地,江阴的变化当然是翻天覆地。我当年生活过的贫瘠乡村,随着城市化的扩大,早已成为城区中的黄金地段。到了今天,江阴的农民很多都非常富有了,跟我那个时代所看见的完全不一样。当年的贫穷说消失就消失了,我所经历过的那段苦日子,仿佛根本没有存在过。
二
三年农村生活,意义非同一般,但江阴并不能称之为我的故乡。
故乡是什么?你在一个地方出生、长大,离开了,回过头再看这个地方,叫故乡。我就是一个南京人,除了两年多江阴的农村生活,在北京的时间加在一起大概有个两年左右,除此之外我都在南京。
我出生在南京的鼓楼医院里面,然后在南京上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以及后来工作,我都在这个城市里。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我有南京情结很正常,但是用故乡这个概念也不正确。就像我经常跟别人说的,我屁股底下总得有张凳子,我站在那里脚底下总归有块土地,那么对于我来说它就是南京。说江阴是故乡其实我是不配的,因为我只有两年多的经历,而且是很幼稚的经历,等我离开这个地方再去看的眼光,其实完全都是一个外人的眼光。
但我和南京的关系就很简单,那就是脚底下这块土地,屁股底下这张凳子,而一个人不可能没有土地,不可能没有凳子。
我的小说也经常对南京有描写。因为你写作的时候总是需要有个地方。
经常有人会问起南京人的特质,我觉得,其实南京人本身没有什么特质。因为我们仔细想一想,南京人和其他城市的人其实差不多。
最简单的一个问题,什么叫城市?
从历史上看的话,城市有两个概念。一个就是“城堡”,比如像南京这个城市,它最早的雏形就是两个城堡,一个叫白下城,一个叫石头城,这两个城堡是干什么的?如果有战争或者什么变故来了,老百姓都躲到这儿来,它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还有一个“市”的概念,就是商业。进入近代就是城市化。城市化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外地人”的集合,像我号称南京人,其实我父母就不是南京人,属于第一代移民。
而且,如果你注意观察,原住民远远不是外来者的对手。也就是说城市的主体是外来的成功者,这个特质是所有城市都一样的。
但是作为小说家,经常会希望在作品里塑造一个理想化的形象,就像我作为一个南京人,我会用文学的手段虚构和塑造出一种南京人的形象。比如说,在作品中我就说,上海被称作十里洋场,到了上海是为了赚钱。但是说到南京,我就说南京这个地方我们什么事都不能干,我们就读书。所以我会写,南京这个地方比较适合于读书。
当时大家都说很好,我们南京人就很骄傲。但是其实这也是一种文学的观点,也就是为了表达出一种理想来。其实这也是我个人的一种理想,我希望能够不要太在乎挣钱、做官这些事,应该去多读点书,这其实是我塑造这种文学形象的缘由。
我认为文学这个东西应该要有一点理想,在我的小说中间,一点光明的东西没有肯定不太好。但是文学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特点,就是要真实。真实就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哪里的人都想做官,哪里的人都想挣钱。南京的很多人挣不到钱,做不到官,就用这句话来安慰自己,其实我们本质上和上海人、北京人都是一样的。
城市化的一个最大特点是为外来者准备的,也是为成功者准备的。这一点无论是今天还是历史上它都是这样。不信你去查一下苏州的那些园林,它们基本上不是最早的本土的苏州人建造的。
所以我们并不能简单地概括说园林就是代表苏州人。仔细一想,园林其实跟真正的苏州老百姓也没什么关系,苏州老百姓也享受不到这些。就算这个园林是他们家的,他们家祖上又不是苏州人,仔细较起真来不就这么回事吗?
当然你会说,一个地方总有区别于其他地方的东西,比如文化,南京的文化,江阴的文化。其实我觉得文化是一个很怪的词儿,它可以有很多种解读,很多时候我们讨论的地方文化其实说的也就是民风的问题。
江阴的民风其实很彪悍,但江阴人所谓的彪悍,并不是“穷山恶水出刁民”的那种强盗的风格。我个人认为它是一种很典型的江南民风。
什么叫江南民风?其实整个江阴、或者说是苏南包括浙江的杭嘉湖平原,基本都有差不多的特点,就是一旦处在和平年代,他们就具有非常强的竞争力,也就是说他们特别适合于在和平年代里去竞争。他们会用一种和平的方式,用他们那种勤劳和智慧去竞争,我觉得这是江阴这个地方最显著的民风。
江阴人不太会去讲天下,江阴人首先是要去改变自己,要富甲一方,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湖南,湖南的民风是以天下为己任,想征服的是天下,所以相对来讲,湖南的经济和江南的经济就有很大差别。这种民风的不同,在我看来也可以说是文化的不同。
当然不同的时代可以获得不同的机会,比如遭遇乱世,或者在一个需要争夺天下要打江山的时候,湖南人就可以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同样一个道理,在一个和平、发展的年代,特别是要发展经济的时候,显然江阴人更可以大显身手。
这种特质也是不分城乡的。我以前在江阴的农村,和一些比我大一点的农民聊天,他们就会说,我们江阴人胆子大,你要问他导弹你会不会做?他们或许不知道导弹具体是什么东西,但他会告诉你他会做,他什么都敢做。
这和苏州人还很不一样。苏州人还是很有理智的,江阴人就是在理智之外又有很多浪漫情结在里面,所以他比苏州人更敢闯。但是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江阴、苏州这些地方都是适合于和平年代,在同等规则情况下适合去创造去伸展。换句话说,就是当大家都搞一样的东西,江阴人会做得更好。
因为江阴离上海近,就像我姨妈那批人都是从农村去的上海,她们的老乡在上世纪80年代正好到了快退休的年龄,再回农村去,就可以把自己的技术带到农村来。其实整个江南农村乡镇企业的技术很多都是从上海这里退下来的,就是我们说的所谓“苏南现象”。
三
还有个态度的问题,也算是文化的一种表现。
我觉得做人是应该有个态度。比如说,你不用太把自己当回事,你不应该觉得你写的小说别人就应该看,因为现在大家都不读书,不看是正常的。那么如果你写得特别好,大家就可能看到。也可能你写得很好,别人没时间的话也不会看,这都是很正常的。
态度是什么,或许可以理解为一种处事的准则。比如我高中时候有一个语文老师,姓陶,字写得很端正,批改作文很认真,对我很关照。他给我解释过“鸟”和“隹”的区别,古音应该怎么读,虽然都和能飞的鸟有关,尾巴上却有区别。鸟是长尾巴的飞禽,隹是短尾巴的鸟。这个解释一直让人糊涂,我总是会想起鸡,想起鸵鸟,凭什么说他们是短尾巴呢。况且鸡的繁体字可以写成“鷄”,也可以写成“雞”。跟祖父(注:叶圣陶)说起这位老师,祖父认为老师说得非常正确,语文就应该这么教。
家里人也会在日常当中传递一个信息,就是做什么都要好好干,认真干,要做一个有用的人。父亲从小给我的一种教育,也是他认为一个人做一件事,不管做什么,即使做一名普通工人,也要非常出色。
所以说,作为一个作者,这个时候如果说要有个态度的话,我认为就是“把自己的活儿做好”,你要对得起自己做的活儿。你写好了都不一定有人看,写不好了别人看了更要扔掉,所以你要珍惜自己干的这件事儿。
在写作这件事上我还是非常认真的。因为它的遭遇是不受自己控制的,我自己能够控制的就是认真把它做好。而我认真的意义就是对得起自己。
在做人态度方面,尤其是家里老人过世了以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的影响是蛮大的。
比如我祖父,苏州人叫阿爹,他80多岁的时候还是整天坐在那里写信。
经常有人说,我有你祖父的信,我内心就一直觉得这件事根本不稀罕,我觉得有我们老爷子的信非常简单,因为他闲着就跟我想聊天一样,谁给他写一封信他都会回,而且是很认真地回,包括谁给他提出一个教育方面的问题或者其他问题,像我大伯养牛的问题,他都会很认真地对待。
他们那代知识分子是很认真的,不像我们身上多少还是有些玩世不恭的地方,我有时候就稀里糊涂的,但我祖父绝对不会稀里糊涂,所以他永远坐在那里写信。我在北京帮他寄信,有时候一天能跑几次邮局,他刚写完就恨不得赶快寄出去。
然后每天到了差不多下午四五点钟,外面就有人喊“戳~戳~”。那个时候北京邮递员拿信的时候要印章,就会在外面喊“戳”,然后我拿印章出去,就会拿一堆信回来,然后这一堆信就变成他要回的一堆信。
我想说的是,他的背影对我的影响很大。今天再回头看的时候,这个80多岁的老人坐在那的背影对我是很重要的。
我父亲过世了以后,我突然发现父亲其实也是这样。我父亲这辈子其实也没写出多少东西来,也没取得过多少文坛的成就,但是做人方面,他也是永远坐在那写东西看东西。写的比看的多,抄过来抄过去的。他有一身坏毛病,写一篇小说或是一篇文章,开头有两句话不对,他就换一张纸又重抄一遍,就是很想写东西。
我的祖父、父亲,他们的背影对我很有影响,所以我现在也是这样的人,整天就坐在电脑前。我眼睛也不太好,我太太经常喊我要注意眼睛。我现在每一页书都是用电脑在读,这个字都是相当于小二的字号,放大很多。
我父亲和祖父,包括我伯父都是这样,如果非要说我家的一个家风,那这个确实可以拿出来说一下。他们坐在这其实没有很强的目的,也不励志,也不为了改变什么,或者是表达一种理想,它就是一个习惯,一个日常的状态。
在《通往父亲之路》这部小说里,我也写到书中的父亲张希夷养牛的一段故事,就是取材于我伯父养牛的经历。
我的伯父是中国社会里很典型的长子,特别有那种家族的责任感,做事很认真,甚至有时候比我祖父还认真。在干校养牛的时候天天晚上起来给牛倒尿,像养宠物一样地养牛,牛养得干干净净,也养得很肥。
我写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并没有褒贬在里面。并不是说我想歌颂什么,我只是觉得有点可惜,他们那时候的知识分子,拿着高薪,去做这样的事情,原本可以做点更加能够发挥他长处的事情。农民也觉得这个事很可笑,农民对牛的态度和我伯父肯定是不一样的,我写这件事情就是一种纪实的写法。如果再解释的话,就是我们怎么把现实生活中的东西化到自己的小说中间去。
现在看网络上的各种解释,有的会说这是一种值得尊敬的行为,认真、负责的态度,会跟工匠精神联系在一起。
时代不一样了,工匠精神同样也不一样。我自己做过4年工人,我对这个东西体会也很深。比如同样是东西坏掉了,我们那个时代讲究的是修,就是依靠技术,把一个旧的东西修好让它可以用。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容易陶醉于这种技术,寻找这种技术,但是你也不得不承认,今天这个时代在“修与不修”的选择上已经多元化了。
因为从商业和产业的角度,商家当然是会推崇“坏了就去换新的”,如果大家的东西坏掉都去修好了,那他们还怎么卖东西?除非像我们这些老家伙,都是属于那种不坏到用不了就不会去换掉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就会有很多消费的概念,去告诉消费者,东西坏掉就需要被淘汰,就不能用了。
四
有人说《通往父亲之路》这本书讲述的是中国式父子关系。中国式的父子太多了,严格说我只是写了其中的某一种,我想写的那一种。
我作品里写的父子关系跟我现实生活体会到的就不一样。比如说我跟我父亲的关系,就跟这个小说里边表述的其实完全是拧着的。
在小说里,儿子张左和父亲张希夷之间是很沉默的。除了一起去中山陵,还有去干校看望父亲这两件事外,张左对父亲几乎没有更深的记忆。小时候的张左被扔给了外公外婆,所以童年是格外“寂寞”的,在他的成长过程里,父亲的角色也是模糊不清的。
但我跟我父亲之间的话就特别多,我父亲也不是个很能干的人,但他是一个跟我一样拉开了就能侃的人。我也是这样,你让我正经做个讲演我就特别不行,你让我一脸正气地说话,那就不是我。我父亲也是这样。
所以我们两个在一起会聊好多,当然文学聊得更多。因为我父亲也是个作家,虽然当时写东西不多,但是他起码一辈子都在写东西,所以我们也经常在一起聊。
我们的父子关系别人通常都很羡慕。但是母亲很不喜欢,因为她觉得我们整天就是没完没了地说,我母亲也插不上嘴,她也经常会为这个事儿不太高兴。
我觉得,我和父亲的关系可以用“多年父子成兄弟来”来形容。所以老父亲走了以后,确实感觉少了一个聊天的人,在的时候也没觉得。
我父亲到了晚年也不是很自信了,每次写点东西都会听听我的意见,会对我说“怎么样,不丢人吧”之类的,经常会说一些这样的话。包括他的作品写出来以后,在发表的时候,都是我帮他拿出去。
印象特别深的是,最早我看他作品的时候我说你这个地方需要改一改,他还不太服气,还觉得自己这样写也行,有时候还跟我争。后来年龄比较大了,慢慢地他也不争了。我说这么改一改,他就说好,你说怎么改我就怎么改,他还挺听我的。
父子关系其实没有什么好不好的问题,这种关系好也是它,不好也只能是它,你总得接受,因为这就是父子关系。
不同的时代也有不同的父子。我算是比较幸运,因为起码我和父亲的“行当”还是靠近的。我爸爸喜欢藏书,我谈不上喜欢藏书,但我很自然地就继承了他这么多的书。我爸爸喜欢读书,我也喜欢读书,我觉得我的人生其实真的很简单,就是写作和读书,阅读对于我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在阅读这件事上,我俩很自然地就会有共同话语,但很多父子就没有这么幸运。比如儿子做生意成了一个大富翁了,我想他除了给父亲提供比较优质的生活之外,对话方面肯定是不如我这种家庭。
但反过来说如果父子俩都是技术工人的话,他们也可能会在如何修理东西上有共同语言。换句话说,恰巧我和父亲都是同一门“手艺人”,我们的手艺就是搞文学,所以我们就很容易聊在一起,这个很正常。
其实除开父子关系,我觉得什么样的人生都是值得赞美的,什么样的人生都是可以去接受的,无所谓好坏,无所谓成功与否。那些都是世俗的东西,从我写小说的角度,或者从我的教养来看的话,我觉得其实内心能充实一些,可能会活得更好。
在小说里,我讲的不光是通往父亲之路,其实也说了这样一个故事。小说里的父亲,他在牛棚里都可以做学问,但是步入老年以后,他什么都不做了,他的学术生命最后就变成一个很空洞的东西。所以,在《通往父亲之路》中间,我隐隐地把这种感慨也写在里面了。
就是对于一个人来说,最珍贵的倒不一定是年轻的时光,而是无论到了什么时候,他没有放弃追求的精神,就像父亲养牛一样。我就觉得不放弃的人生永远是优美的。
我大概想表达这样一个意思,向永不停顿的追求表示致敬。到后来的话,文中的父亲只是变成了一个学术偶像,一个那种所谓的“成功人士”,看上去很光鲜,但是他自己内心是不是很充实又是另外一回事儿了。
所以说,“通往父亲之路”,它本来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它有点像火车的两条铁轨,从远处看过去的时候,希望到前面能够接近父亲,但是走着走着发现永远走不近,永远是这么大的距离。也不能说距离越来越大,但起码它没有改变。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凤云 陈艺娇整理
本文采写得到译林出版社大力支持
版权声明:本文系农民日报原创内容,未经授权,禁止转载。任何单位或个人转载,请致电010-84395265或回复微信公众号“农民日报 ID:farmersdaily”获得授权,转载时务必标明来源及作者。如有侵权,本报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公众号“零度往上”

